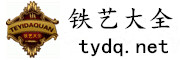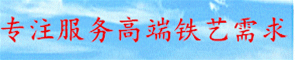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谢白曼(Feike Sijbesma)出现在本报记者对面时,这种动力背后的关键推手跃然而现——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奔走在达沃斯夏季年会多个活动,只能在晚间接受这次专访的他,能量十足,53岁的这位典型北欧绅士还十分幽默。
谢白曼领导着全球23,500名员工创造着约90亿欧元的年销售额,可他对于中国有着特别的热爱。不仅是因为这里是公司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和创新中心,他更是真诚地愿意将自己及公司积累的如何成功转型、开放式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同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分享。
“帝斯曼主业变换但基业长青的秘诀是,和中国一样我们制定五年计划——每五年作为一个周期,我们会展望未来,不断反思,问自己一些根本性问题。”类似拿中国做比或举例的话语在谢白曼的回答中比比皆是。对了,他还是我所采访过的全球CEO中最喜欢举例讲故事的一个。
谢白曼是如何讲诉一家全球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跨国公司转型、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故事的呢?他对未来的战略、愿景和面临挑战又有哪些想法?在本次专访中他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
长青基因
《21世纪》: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提到,“生物能源和生物医药”两个领域会不断壮大,甚至改变公司现有核心业务。能否具体谈一下公司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蓝图、路径和目标?
谢白曼:我们认为,生物基业务和生物医药是两个崭新的增长引擎,帝斯曼有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业务,还有创新中心,其中就包括生物医药和生物基业务。
近一百年左右,通过生物医药和公共卫生等方法,人类提高了健康水平、延长了寿命,我们终于能够活过40岁了。但是,我们身体的运动机能和身体部件,还是受到自然界的限定,到了85岁,臀部等有些部位都很难保持灵活。我们要用创造性的方式更换这些部位,我们因此要开发新的材料,我觉得这个业务领域有很多机会。目前,这个业务还只在美国开展,但我想很快就会进入欧洲,以后也会进入中国。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基。世界资源很有限,世界经济要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就要开发可再生资源,生物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农民种庄稼只是收成其中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开发了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庄稼的废料,转化成生物燃料,但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第二代废料,我们可以继续收集,从中提取蛋白质等。通过微生物技术,循环多次利用庄稼,发展生物基经济。我觉得这是绿色的革命。
目前,这两个行业对于我们是比较小的业务,但我们预期到2020年将达到现在的十倍。
《21世纪》:帝斯曼通过不断的出售和并购,主业变换但基业长青。这种公司基因是如何形成的?
谢白曼: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十分复杂。帝斯曼至今已经有111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转型,最早是一家煤矿企业,然后变成石化和大宗化学品公司,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公司,主业变换但基业长青的秘诀是,和中国一样,我们制定五年计划——每五年作为一个周期,我们会展望未来,问自己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我们现在所处的行业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我们的行业会不会出现新竞争对手,我们自己提出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也要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反思。当我们是煤炭公司时,我们发现了煤炭的市场将被石油天然气所取代的趋势,于是及时切换到新的业务领域。但我们会继续追问新行业有没有未来。当我们进入石化行业时,公司盈利非常好,业务开展十分顺利,但我们还是会质疑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们会想,新一代的阿拉伯领导人很可能为他们的国家留下一些遗产,包括沙特和卡塔尔,我们觉得,如果他们不把石油直接卖掉,而是将石油加工成石化产品,他们的竞争力是十分强大的,所以,我们必须适时考虑退出这个行业最终我们及时退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从某个行业退出的时候都是太晚了,这时这些行业已没有太大价值,这时候再做出退出的决定容易,但卖不到好价钱,无法推动公司未来的转型。
我们经常问自己一些艰难的问题,但我们能做出及时的决定,做出必要的改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其中牵涉到许多因素。要实现企业转型,你还要关注公司管理层和领导者。有些领导者或管理层擅长从前的业务,但他们如何对新业务也擅长呢?转型时,要对公司里的许多人加以教育,有些人必须调整,而管理层的过渡和转型也很重要。
同时,也要关注公司的文化。例如,过去当我们从事石化行业的时候,卓越的营运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降低生产成本。我们也讨论过我们要不要以市场为导向呢?那时我们说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如果在石化行业实行市场导向,那也许会误导我们,因为在石化行业,投资基建需要五年的时间,要花五年时间思考,再花五年时间开发,可能要花费一二十亿美元,才能开发一两种化学品。 十年后,你的销售人员说市场不再需要这个,而需要那个。你也许会说,不行,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开发两种产品,如果他们需要,好极了,如果他们不需要,也没关系,我们降低价格也可以销售。那时这是个风险很大的业务。现在,我们经营精细化学品或生命科学,和不同的工厂合作,投资额度大多几千万美元,而不是几十亿美元,如果市场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我们就改变合作工厂。而现在如果只追求卓越经营,低成本经营,你也可能因为不够敏感而错过许多市场机会。
转型是十分复杂的,许多公司曾经失败过。在这个过程中,帝斯曼积极倡导创新,我们一直倡导开放式创新理念。许多人想产品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发明,这样,他们的研究人员会感到很自豪,但我们认为,如果在其它地方找到好的创新,也可以有自豪感,这样还会刺激合作。这种开放的创新方式十分重要。
我再举一个例子。许多创新是在毫无征兆的领域发生的,没有什么线索。例如太阳能,我们过去曾经开发了一种新的画框涂料,就是挂在墙上的画框,这种涂料不反射光线,所以你看画的时候会觉得很漂亮,这种涂料很漂亮,但很贵,用这种涂料的画框比同类产品要贵六七倍。漂亮是很漂亮,但人们说我们不会花这么多钱买这种画框。所以,我们决定为这个创新项目举行葬礼,停止这个项目。但是在葬礼上,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项目?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涂料用到太阳能电池上去,这种涂料不会反射阳光,太阳能不会损失,传输率会很高,于是我们就将这种涂料用到太阳能电池上,结果很成功。所以说,创新有时在意料之外发生,你要有开放式思维,如果你没有开放式思维,你就会错过市场机会。
创新秘籍
《21世纪》:你刚才提到创新,全球强调创新的公司都有一些独家秘籍,如谷歌有个“创新实验室”。你们在创新方面的秘籍是什么?
谢白曼:我们每三到五年要审查我们自己研发能力,要看看三、五年内公司内部有没有足够的技术,是否足以形成创新能力。有时候,我们不具备某种技术,但需要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就为研发人员提供良好条件,给他们充裕时间去自由思考。对一般人员要规定研发期限,但真正优秀的研发人员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利用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用什么事都报告,这些人有时候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突破。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一半的自由,我们说,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但有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你们开发某种产品,成本必须在五美元以下,只要低于五美元,你们从外面找来也行。我一定要有创意,要满足人们20年内新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提一些基本条件,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就解放了他们的思想。
此外,现在我们持有大约20-25个小公司的5%-20%左右的股份。我们不去太多的干涉他们,只是在董事会里。有时候,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得到灵感,懂得新的哲学。有时我们发现投错了,就把它给卖了,承认错误就行了;有时我们觉得这家公司不错,就把整家公司买下来。你看,风险投资也是实现创新的一种途径或者工具。
我们不要将创新停留在公司总部的中央实验室里,我们希望能在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重要区域实现本地化创新。现在是本地对本地创新,我们希望以后能变成本地对全球创新。我们只在几个重要国家进行本地化创新,包括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其次是印度,我们也关注巴西、美国和欧洲。
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公司连续6年位列全球可持续发展公司榜单之首,是如何做到的?
谢白曼:帝斯曼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巨额的资金,到2015年,至少有50%的现有业务的生态足迹要大大优于竞争产品,其余的50%与竞争对手相当。换句话说,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毫不吝惜,这样做对我们帮助很大,如今,帝斯曼的股票表现相当好,我们的盈利十分出色。而且如果你是关心地球、关心社会的企业,你就可以拥有积极向上的员工,我们员工向心力调查结果表明,我们的员工凝聚力、积极性很高。所以我们已经证明了可持续发展和财务表现中间不存在矛盾。
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能够让我们不断进步、进步、再进步。4年前,公司将我和同事的收入要和可持续发展挂钩,一半收入看财务表现,一半收入看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坚持一贯很重要,要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1世纪》:对于很多中国公司(尤其是能源、材料、化工业)CEO来讲,投入可持续发展意味的是成本而非收益。你从自身的经验如何说服他们自发自愿的去选择更环保的发展之路?
谢白曼:我认为,可持续发展不能只关心成本,更是公司的价值观,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未来发展机会!如果你关心爱护下一代,你就要可持续发展。即使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成本,但你也得做好,你首先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但是,可持续发展不一定总是花钱的事,有时候你也可以利用可持续发展作为业务增长引擎。我愿意向中国更多的企业家分享这一点,我们在许多场合包括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推广我们的企业哲学,希望与更多企业家分享这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