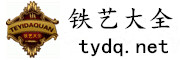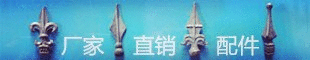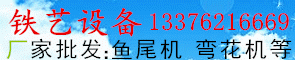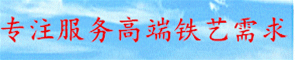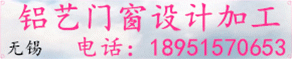⊙记者 陈俊岭 ○编辑 张亦文
从中国最广袤的乡村视角观察,“城镇化”正潜脉静流在城乡每一处不显眼的角落。今年中秋假期,记者再次回到位于河北邯郸的家乡,切身感受到涌动于城乡间的人流、资金流的深刻变化。
与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大中城市不同,记者也注意到,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所挣来的资金,更倾向于回流到所在的家乡城市,这也带动了三四线城市楼市、车市,甚至电影票房等消费市场的繁华,随之而来的还有,三四线城市的天际线与财富观也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
乡村消逝的人流
纵横交错的水泥路、昼夜通明的路灯、直达城市的公交……尽管现在农村的生活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但仍挡不住村民们外迁城市的冲动。
中秋假期,记者回到位于河北邯郸东部某县的家乡,再次近距离感受到农村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过,行走在村子大街上,仅见稀稀落落的人,却随处可见荒置的院落大门紧锁,一打听才知道人家早已搬到城里住了。
农历八月十六这天,正逢村里有人办喜事,尽管当天前来贺喜帮忙的亲戚邻居不少,却少见20岁上下的年轻人,闹洞房当晚照理要在村子里放电影,但前来观影的村人更是屈指可数,与记者小时候的热闹景象不可同日而语。
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村里一位老者对记者解释称,由于做农活赚不了钱,年轻人大都不愿呆在农村,他们纷纷到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打工去了,比如有人在北京做快递月收入都在4000元,还免费提供食宿。
“尽管现在的农村越来越接近城市,但教育医疗等配置仍与城市相差甚远,更不用说工作机会。”于是,在首批淘金大城市村民的财富效应带动下,很多有条件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农忙或春节时才回家,中秋、“十一”根本没时间回来。
外出务工资金回流
与分布国内各地的广袤乡村日渐消退的人流相比,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大中城市却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地处北京北六环外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记者老家的阿鹏正从事一项简单却并不繁重的体力活。前几年,他曾南下福建、广东等地打工,但随着制造业的下滑,阿鹏也和无数打工者转战用工和待遇更为稳定的北京。
对于三十出头的阿鹏来讲,家乡仍是他最牵挂的地方,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仍在家乡,而打工所在的北京只是他赚钱的地方,每逢春节他都会将在自己在大城市打拼赚来的钱带回家乡,来改善生活,现在他的孩子正在县城读书。
“留在北京,我从来没有想过。”阿鹏看着工地附近已经直冲三万的房价毫无思索地称,不过在这里赚钱在县城买房,还是能指望的,目前他所在的县城房价均价不足三千。
阿鹏的想法也代表了家乡外出务工者的共同心声。记者注意到,与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大中城市不同,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所挣来的资金,更倾向于回流到家乡城市,这也带动了当地楼市、车市、甚至电影票房等消费市场的繁华。
两年前,世界五百强沃尔玛在邯郸最繁华的商圈开设了首家店,受其带动,苏宁电器、新天地电影城等知名品牌商也纷纷入驻,这里也成为不少从大城市退居三四线城市发展的年轻人的休闲好去处。
而在这些繁华的商业中心附近,也鳞次栉比矗立起不少新起的楼盘,不少从乡村出来、并曾在大城市奋斗过的年轻人正成为这里的新业主。
时至今日,尽管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争议仍不绝于耳,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城市周边乡村汇集而来的“人流”,以及从大城市回流的“资金流”,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些城市的天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