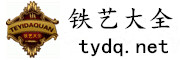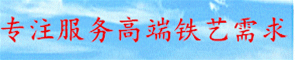前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允许该省“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至此,允许“双独”生二胎,在全国实现全覆盖。有媒体报道此新闻时说,此曲折经历“足以管窥中国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前路艰辛”。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是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尔萨斯不过是建议,其他国家也未有积极响应,至多不过是号召和鼓励人们节制生育而已,而在中国则成为铁的国策,这必定是因为它在中国找到了生长的土壤。这种土壤,就是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家权力管制和干涉家庭人口和规模的措施却是几乎代代有之的。
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商鞅就在秦国实行“异子之科”,要求成年兄弟分户单过,否则予以加倍征税的处罚。这是利用税收手段强迫建立小家庭;汉朝为了鼓励生育,对于15岁到30岁之间的未婚女子,征收比正常人多一到五倍的税赋;从《唐律》到《大清律例》,都一直规定:“父祖在世,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简单地说,就是祖父或父亲在世的时候,法律禁止儿孙们分家分财。原因是,古代的某些赋税尤其差役是按照户等高下分配的,而划分户等高下的依据就是家庭财产和成年男丁的数量。上户的赋税和差役负担要远远高于下户的负担。一些家庭为了逃避赋役,分家分财因而降低户等,而国家为了征税派役,就规定父祖在世,禁止分家分财。
通过法律和税收等手段,操控家庭的规模和人口,与国家权力赤裸裸禁止老百姓生育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看看晚清时期汪士铎的建议,这之间的对接就可以理解了。汪士铎在其《乙丙日记》中向政府建议:“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
从历代国家干涉家庭规模,到清末汪士铎建议国家鼓励溺婴,到100年后酷烈的一胎化政策,体现出马尔萨斯思想在中国能够扎根的原因:在这个国度,国家权力深刻地介入私人家庭生活,历史悠久,轻车熟路。
国家权力强力介入到最为私人化的生儿育女的领域,虽然取得少生几亿人的成绩,或许减轻了一时的经济压力,但是,其后果是严重的。不难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人口严重老化,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劳动力严重不足,工作的年轻人人数不足,不堪重负,庞大的老年人群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这种严重的后果,让人想到哈耶克终生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哈耶克批判的建构理性是一种事先精密计算,试图对社会秩序进行“设计”的理性。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为什么会如此?哈耶克说,因为个人知识的不完全性、局部性、分散性和异质性,使得人类无法集中处理整体性知识,因而也就不可能建构社会秩序。
在中国,因为传统上是一个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建构理性主义者与权力结合起来,更加强化了权力无所不能的傲慢与自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谓是哈耶克所说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绝佳样板。因为政策设计者即权力的掌控者自身知识的局限和他们处理整个国家未来复杂问题的能力的缺陷,再加上权力的致命自负,以及中国特有的权力依赖症和权力崇拜症,更强化了他们当年设计的计生乌托邦的悲剧性灾难性。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 昭示出对这种乌托邦政策的调整,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