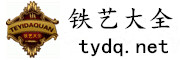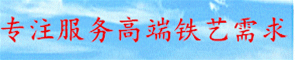防治前提:
对相关信息翔实分析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儿童虐待信息都有翔实的数据统计,而我国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
我国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重视虐童问题,但一个令人惊讶而尴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虽然我国和儿童福利与服务相关的机构众多,有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儿童工作部,如民政部儿童福利处、卫生部妇幼保健司,还有全国青联和共青团组织少年部,妇联也设有儿童部。但直到2010年,中国的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才建立起来。
这就导致当媒体或公众甚至是研究人员谈论虐童问题时,缺乏严谨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日两国研究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中日儿童虐待状况的分析与比较》中,就不得不通过“在两国出版刊物上统计儿童虐待案例”的办法收集数据。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据推算,中国受虐待儿童数,可以千万计”这样的模糊说法,竟是依托网络调查样本分析得出。
而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专业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从事这样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这些数据都对社会公开。
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也会每年公布虐童情况数据,而且他们公布的速度更快。今年8月1日时,就已经将上半年的数据公布出来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国内媒体每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虐童数据时,就惊呼“日益严重”或“创历史新高”。实际上,完全没有统计资料才是最可怕的,无的放矢,怎谈防治?
法律规范:
各项规定日趋细致严格
防治虐童的法律,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朝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的,举报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大、虐待的标准也日趋严格。
美国社会开始重视虐童问题,是因为一名叫玛丽·艾伦·威尔逊的小姑娘。她被养母毒打虐待将近8年,然而当社会各方准备组织营救她时,却遭遇了“没有保护受虐儿童的法律,却有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尴尬现状。玛丽案结束后,美国迅速开展了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
1963年,美国政府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1974年时,美国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该法要求各州都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虐待与忽视最低的定义。1984年,《儿童保护法案》通过,比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还早5年。
在美国防治虐童的相关法律中,最有特点的一条是“强制报告制度”。报告的人员范围在不断扩大,举报的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细化。另外,大多数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视时也要举报。其中还规定,对儿童有责任的人或组织面对虐待和忽视时要举报。对于知情不报者,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
于是,我们经常听说一些这样的例子:刚去美国不懂规矩的华人,在家里刚“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只是去超市购物把孩子忘在了车里,就立刻会被警察围住,被当成虐童嫌疑人,十分尴尬。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美国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爱“打小报告”的国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儿童保护法案十分严厉,在比较严重的状态下,法庭可以下令禁止施虐者回家,如果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儿童将被带离家庭。
更令人感动的是我国香港编制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描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这与我们制定的“宏大叙事”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建构体系:
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参与
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被整合进来。
翻阅2011年香港虐童统计可以发现,有55%的施虐者,都是受害者的父母。不约而同的是,美国现行的儿童保护措施,也是尽量以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因为实践证明,家庭始终是孩子成长的最佳场所。
这就难免会存在政府所无法触及的情形,即便法律再完善,也没法确保所有的角落都被公平与正义照耀。于是,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就必须整合进来。
令人吃惊的是香港,其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从服务数量看,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而更有意思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社会组织以企业模式经营,并要面对来自其他同类组织的竞争。市场的力量,在香港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与一些拥有成熟保护体系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儿童的福利服务多集中在助学帮困方面,对虐待防治问题重视不足。不仅尚未建立有关儿童虐待的监测和报告系统,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严重缺失,系统的儿童保护体系尚待完善。新京报记者 李慧翔
美国
举报虐童人人有责
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设的儿童及家庭管理局,自1995年起,每年公布全国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状况。他们提供的数据不仅将受害者按照年龄、种族、性别等属性进行了划分,还将施害者同样进行了统计,并计算了两者的关系。公众可以在相关网站上动态地浏览每个州的数据。
在虐童“强制报告”方面,早期的报告主要来自医生的举报,因为只有医生才具备相关被虐待的医学症状的知识,他们会在发现孩子身体受到伤害时进行举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的法律都拓宽了举报人的范围,主要扩大到一些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专业人员,如幼教、中小学学校老师、警察、机构保姆、一些照顾孩子的特殊社会服务机构人员等。
报告的内容也在细化,美国最早仅仅要求对残暴殴打和身体伤害进行举报,后来则要求身体虐待和忽视都要举报。如今的举报范围则更加宽泛,如儿童处于人身危险、儿童没有得到必要的照顾和监管、儿童经历严重的情绪问题等。
资金来源方面,美国通过传统的法律拨款程序,给州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建立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的项目。各州都在想办法增加儿童信托基金的收入,特别是一些附加税,比如像结婚、出生、离婚等交的费用,或利用州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人们自愿捐赠。资金完全采取收支分离,严格进行监管,且会特别标注这些资金专门用于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
日本
社会组织积极干预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大阪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全国儿童相谈所等政府部门或机构都在关注虐童问题。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信息情报进行统计。日本厚生劳动省从1990年开始对儿童虐待数据进行了统计,并逐年公布。
2000年,日本公布并实施《虐待儿童防止法》,经过4年的使用后,在2004年进行了部分修改。和美国一样,日本的法律也是朝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的。比如在修改前的虐待标准中,规定了“如果发现有虐待的必须举报”,修改后就变成“认为有虐待的必须举报”。同时,语言暴力也被列入虐待标准。
日本的社会力量在应对虐童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1998年在日本成立的“儿童虐待思考协会”,就以儿童虐待为题材制成漫画,向志愿者介绍虐童工作现状。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设立儿童访谈热线,与一些儿科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联网,及时倾听虐待儿童的举报。此外,有关防止儿童虐待工作的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经验交流会、论文发表会、学会等集会也在日本全国各地经常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