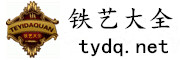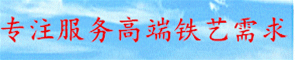其三,风险预判的大幅失准令人扼腕。比风险本身更危险的,是对风险的预判失准甚至误判,因为预判失准不仅将导致宏观决策者和微观主体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还可能会不经意间放大固有风险,或形成新的风险裂变和风险传染。纵观2012年全年,风险预判明显失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核心风险构成预判失准,2012年年初乃至整个上半年,市场将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定位于欧元溃败、希腊退出、通胀逆袭和谁将成为下一个希腊,而年末回首,2012年的核心风险唯有经济增长广泛、持续和难以遏制的失速。二是对波动性风险骤升预判失准,2012年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股指等国际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市场震荡和异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了预料之外的冲击。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市场对欧元区内德法核心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徒增、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
其四,尾部风险的集中爆发引人瞩目。从结构上看,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尾部风险分布广泛、爆发密集,第四季度甚至可能成为2009年第二季度次贷危机见顶消退之后全球经济最难熬的一个季度。尾部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财政悬崖的山雨欲来,这个岁末年初,美国前期减税政策的到期和自动支出削减机制的启动将带来6000亿美元左右的政府支出骤减,基准情形下恐将对美国经济造成1-1.5个百分点的增长损失,恶化情形下甚至会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财政悬崖的危险在于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且受制于跛足政治结构,求解时间过于紧迫;二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恶化,2012年第四季度欧洲边缘国家迎来新一波偿债高峰,债务风险再度放大,而三驾马车在希腊债务削减上的矛盾渐深、希腊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放大、救助机制对救助条件的苛刻要求、核心国家在自身增长乏力背景下利益输出主动性的大幅下降、欧洲统一货币区体制完整性的裂痕渐深又进一步导致了危机潜在恶化;三是新兴市场复苏的期望落空,第四季度作为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承载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触底、复苏反弹的市场期望,但随着经济失速的超预期演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高速起飞阶段深层积累的脆弱性风险持续释放,进而使得市场的拐点预期难以实现;四是全球经济信心的超调受损,受以上三重因素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活跃度也随之下降。
其五,结构失衡的逆流而变发人深省。2008年以来,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充分彰显了结构失衡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破坏性,而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方向也集中于结构失衡的改善。但在傲慢和偏见的影响下,在全球经济自由落体的作用下,2012年出现了三大逆流:一是在经济结构上出现南北失衡加剧的逆流现象,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7%的经济增长,增速高于2011年的1.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实现2012年增长率提升的国家,超预期反弹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使得美国经济在危机中的影响力不降反增。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出现单极影响力增强的逆流现象,2012年,多元化更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景,而非切实推进的现实,欧债危机的不断恶化导致欧元影响力大幅下降,作为全球第二重要的货币,欧元的存续都受到了市场质疑,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出人意料的持续下滑,又使得新兴市场重要货币的波动性明显加大,崛起速度悄然下降,例如人民币就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首次贬值之后,又于下半年以连续涨停的方式重回升值通道,国际化进程里的波动性风险骤增,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反而并未出现预期中的明显下降。三是在金融深化领域出现虚拟与实体脱节加重的逆流现象,2012年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态势,一定程度上优于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经济虚拟化的风险悄然上升。